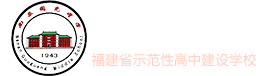校长专栏
留在生命深处的历史印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60年琐忆杂谈
发布时间:2009-10-13
阅读 : 23402
留在生命深处的历史印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60年琐忆杂谈
华东师范大学 叶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教育发展史,是起伏跌宕、可以大书特书,值得深思、慎思的大历史,但又是很难有哪一篇有限、具体的文字能说得清、道得全之史。然而,对我们每个有幸同共和国一起走过60年的个体生命来说,这却是一段亲历亲为的生命史。共和国60年教育发展的宏大历史。交融化聚在每个不同个体的生命深处,在我们每个不同个体的精神世界和个性上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铸就了我们这些“40年代人”的精神气质。也许,这是最能说明60年教育之生命意义,也是我可以做出的最佳叙述角度之选择。因为这60年中我没有离开过教育领域。
出生在抗日战争中期的我.尽管4岁时就迎来了抗战胜利,但却因年幼而未留下任何印象。我生命中第一个记住的国家喜庆的大日子,就是上海解放那年,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当时作为三年级小学生的我,最爱看的就是国庆大游行:欢乐的秧歌、舞动的腰鼓、漫天的红旗、嘹亮的口号,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欢腾喜庆的浓烈画面,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这就是我们高唱的“解放区的天”。它给我幼小的心灵涂上了一层明亮的底色。
第二年,我9岁,戴上红领巾,成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从此,每当高举右手向国旗行队礼之时, 蒙陇地懂得了崇高与伟大;从此,羡慕革命先烈轰轰烈烈的人生,知道了刘胡兰、董存瑞,读遍了《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等抗日小说;从此,参加了许多次“重大”的队活动,从挨家挨户请叔叔、阿姨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到捐献废铜烂铁制造飞机大炮抗美援朝……几乎当时所有的国家大事。都有少先队员可参与的方式。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六一”庆祝活动和联欢晚会,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就是我们的节日盛装。这条红领巾我一直戴到高二满15周岁离队。我 热爱这个我人生中参加的第一个组织。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在小学上些什么课。真的是没有清楚的记忆了,但这一次次的活动场面却记忆犹新、清晰生动,还包括当时的心情。最近读到一则以“怎样让孩子们关心政治”为题的文章,文中提到了与08国际峰会几乎同步召开的08青少年峰会,并提出国内的重大政治活动,如人大会议等也可邀请青少年、儿童参加。自然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对培养未来的政治家也许特别有意义,但我更喜欢的是自己儿童时代,每个少先队员都能投人的,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我们这些不懂政治的孩子所参与的政治活动。它让我们的视野扩展到校外、社会。它让我们在自主参与和积极投入的新鲜活动中。懂得了爱祖国、爱英雄,恨侵略者、恨敌人。这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对每个公民最基本的认同教育。直至今天我还认为,解放初期对儿童的思想教育是成功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的说教,并不停留在学校,也不限于少数学生参与。正是这样一种孩子喜欢参与的活动,不仅使我们根本没有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而且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幼小心灵中,播下了对国家、民族、事业负责任的种子。因为英雄已留在我们的心中,理想似乎是人人长大不可缺少的东西。对照今天的教育,这些来自当年儿童的体验并非毫无价值。
我的初、高中阶段是在学习苏联的全盛时期度过的。影响我们精神生命成长的首先是学校的环境与课程,高中阶段尤甚。教室里的课桌椅是单人单座、椅背连桌的那一种。课程都模仿苏联,如将语文分为汉语与文学;地理分为自然地理、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等。外语则一律开“俄语”。老师上课按照凯洛夫“教育学”的五段教学法进行(我大学进了“教育系”才恍然大悟这一点)。每节课都有5分钟老师抽号提问,采用五级记分制,每节课老师都带着《教学日志》进教室,显得特别有精神。当时十分强调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落实。小测验几乎天天有,但很少超大纲,基本属于复习、巩固。尽管没有太多的创造性要求,但这种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学科知识、技能训练,确实使我们形成了有关一门学科确定性的基础性素养,这些素养成为我们入大学进行专业学习时,向其他领域拓展的基础性支撑,至少不会害怕,因为我们学过。它是我们曾经进去过的“邻家大院”,我们知道这些学科领域的一些最著名的奠基人物,对他们的敬仰和对真理的信服,使我们养成了理性对待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
现在看来。在青少年成长发展的初期,基础性的学科素养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人会没有认识世界的根基。今后个人的成长,以及不管他在什么领域的批判或创新。都是针对“有”而不是“无”。一个人的批判、创新能力也是建立在自身的“有”(包括知识、经验、见识、勇气、智慧等)的基础上,而不是“无”。缺乏“有”之基础的批判或创新,很可能走向狂妄、破坏或几近于空想。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有”的基础积累与形成的最佳时期是儿童与青少年期。也许,这正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教育界最初的强烈反应就是要重新评价凯洛夫;这正是在每次教育革命过度狂热以后,开出的良方总是回到基础的根本原因。文化要传承发展、个体要成长发展,都不能没有基础。
自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当时的中小学教育是最好的。并不是说学校只要完成基础教育的“双基”任务就可以了、凯洛夫教育学是无瑕可击的。强调“必不可少”,并不等于只要有这些就足够了。如果当时的教学思想有什么大不足的话,那就是缺乏开发知识内涵的(而非贴标签式的)培育人精神世界发展的丰富t多样的价值,仅仅满足于知识、技能的传授与掌握。这种教学思想因来自行政力量组织的宣传、学习、讨论而内化到大多数教师的教学行为中,且由老教师传到新教师,成了学校教学的一种常态。我们如果在学习某ˉ门课程时产生兴趣的话,常常得益于好老师。他能在教学中把我们引向更广阔的世界:吸引我们去参加课外活动小组:指导我们不用死记硬背,而是掌握学习这门学科的方法:让我们在学习中产生兴奋、愉悦与成功感。但毕竟这样的好老师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使在我求学的华东师大一附中,也并非个个老师都是如此。庆幸的我还是遇到了一批好老师:在我们的老师中。没有一个讲不清楚自己承担的课程:我尤其佩服数学老师思维的清晰和不用圆规就能画出一个漂亮圆的绝活,尽管我的数学成绩并不优秀;我喜欢俄语老师对我们的亲切和巧妙的指导,尽管我的俄语也学得一般:特别让我庆幸的是。我遇到了∷位优秀的教中国近代史的老师。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游击战和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精彩讲述(到大学后,学习了《毛泽东选集》,才知道老师是将毛泽东思想补充到了教学之中),使我一下子改变了历史要死记硬背的看法,看到了历史的智慧,将我对文科的兴趣,从纯粹的爱好文学,提升到爱好智慧,坚定了大学考文科的决心。
初、高中阶段形成我精神世界的另一重要源泉,是课外所阅读的大量苏联小说。当时尽管我们的课程并不比现在少,也不文理分科,但课余的时间还是不少,作业一般晚饭前能完成,晚上和星期日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读小说成了我最大的满是。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无脚飞将军》、《匪巢覆灭记》,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不是苏联小说的《牛虻》,都是我们广泛传阅和被深深吸引与震动的作品。不只是情节描述、警句、人生格言,还有小说主人公那种对祖国、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那种绝对超乎常人意志的高大形象,像刀一样深深地刻在我们敏感的心灵之中,成了鞭策我们努力和克服自己缺点的力量。尽管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并不懂多少人生,但心中有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追求,知道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英雄,都会过平凡的生活,但平凡不等于平庸。我想,这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人格力至和精神财富:不甘平庸;愿意克服自己的不足。积极向上;看重精神世界的享受与满足;愿意为国家和人民(尽管还都是较抽象、笼统的概念)奉献自己的力鱼;从未想过个人要置于国家、人民之上。这个年代的青少年,大多是先形成“大我”意识的人。
1958年。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我跨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大门,成了教育系的一名学生,从此。留在这所大学和教育领域,由大学生到大学教师,由青年教师到老年教师,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大起大落的50年。
在1958到1978的前⒛年,从“三面红旗”、反“右倾”到三年自然灾害、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从批修反修、 “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都成为我大学生活的重要构成。大量的运动要求我们经常下农村劳动,参加“四清”时还吃住在农民家中,这些深人陌生农村的生活,令我终身受益的是结下了“草根”情结。在我的精神世界中,有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艰苦的劳动磨炼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体力。如此激烈动荡的政治大风大浪,让我从大学生时期开始,逐渐清醒和懂得:政治不只是光辉理想,并非只有伟大英明,还有复杂尖锐的斗争,阴谋毒辣、直至残酷到你死我活的血腥。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有过的走出“政治幼稚病”的时期。但其代价,无论是国家、社会,乃至家庭、个人都太大太大。这一时期中,业务上除了大学期间的各门课程学习,获得了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基础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有了一些治学的基本训练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进展。专业理论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思维方式简单化和模式化,成了自己专业素养上幼稚的典型特征。是中小学养成的好读书的习惯和大学的环境,是运动前前后后相对正常提供的一些时间,使我还有可能阅读到各种可以借到的书,从而精神生活还未被完全沙漠化。20年政治化生活的结果是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代特别的大学教师:做了十多年无太多“教”可“助”的“助教”,直到40岁前后,才开始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学术上的贫乏和幼稚,才开始重新启动和学习审视已有的一切,努力去把失去的时间抓回来,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努力尽快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教师。这是历史造成的一代大学教师的“集体学术迟到”。
最近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巨大的历史代价,终于换来了政治路线的调整和一代知识分子的清醒。尽管教育领域面临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时代剧变带来的复杂挑战;尽管教育发展还一直有改革伴随;尽管在前行的路上还常常让我们感受到来自专业领域外的、非学术的干扰和折腾:尽管还有不少已成习惯的、令人头痛的管理制度、作风和各式弊端的侵蚀:尽管我们也还有迷茫、困惑和苦恼、犯错误的时候,但我们一起走出了百废待兴的时期,逐渐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术空间;有了自主选择开展学术研究的可能;有了更多可以沉浸于专业的时间;有了不断拓展和更新学术视野、进行学术交流的可能。逐渐地,我觉得自己有了专业思想,有了理性反思和批判的能力,有了学术的 “自我”,有了一种被新的时代唤起的、在自己专业领域中做一个发展专业领域的奋斗者的勇气。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经历了60年风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走向成熟,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未来中国,需要我们一起来创造。尽管我已走近教师生涯的终点,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大我”意识、“英雄”崇敬和“草根”情结,又在心田中萌发,只是多了一份清醒与从容。它成为一种力量,推动我抓紧最后一段的工作岁月,尽自己的力多做一些,做好该做和能做的事。
我从自己的60年人生中,体验着教育对于个人生命的独特价值。知识、技能的习得、运用和发展是人生一辈子不能没有,且是易见、易识和可变的。但教育,尤其是青少年时代所经受的教育,对个人心灵、精神、气质的孕育,却留在生命的深处,在需要的时候,它会唤醒内在的力量,以一生的积累和独特的姿态,去回应所面临的时代,去圆心中的梦。
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有不同的历史印痕,但只要是生命深处的历史印痕,就会永远活在自己今日的生命和行动之中。
(责任编辑 梁伟国 刘 群)